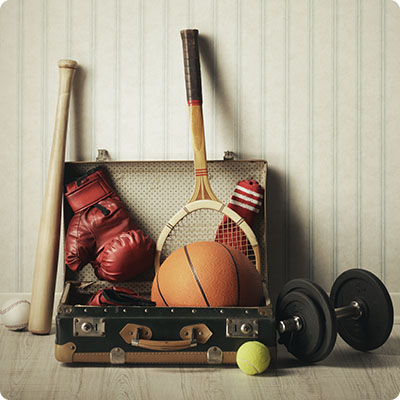从口口相传到第一批书面文件
在成为欧洲人羡慕的对象之前,苏里南已经有几个独特的土著群体定居下来,特别是阿拉瓦克人和卡利纳戈人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口述传统,有时是萨满教的,有时是传说的,如《Contes arawak des Guyanes》(由 Karthala 出版)一书中揭示的那样,我们惊奇地发现,人可以变成美洲豹或鹦鹉。随着殖民化的到来,奴隶制也随之产生,从奴隶--然后从他们的后代(无论是马龙人还是克里奥尔人)--中诞生了一种不同的口头文学。非洲裔苏里南人的温蒂教--类似于我们更熟悉的海地伏都教--就是其中的一部分:据说世界是由阿纳纳-凯迪曼-凯迪扬蓬创造的,世界上居住着各种神灵。同样,尽管阿南西起源于西非民间传说,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也能找到阿南西的形象,它交替出现在人和蜘蛛的外表中。这种精神或神话体有时与舞蹈和音乐相结合,甚至与 "嘟 "剧(doe-theatre)中的戏剧表现形式相结合。1863 年后,这一剧种演变为拉库剧,新的原型如Snesi(中国人)或Koeli(印度人)在其中扮演了角色:奴隶制的废除导致了一种不再冠以奴隶之名的奴役形式,新的 "工人 "从亚洲大陆招募而来。在苏里南,这些遥远的传统又产生了不同的版本,如借鉴自爪哇的皮影戏wayang、马舞jaran kepang和印度音乐风格baithak gana。
人口的交融不断灌溉着口头传统,书面文学也在这片沃土上萌芽。除了借鉴了埃尔多拉多神话的第一部旅行记述和某些日记(包括荷兰旅行家伊丽莎白-范德乌德(Elisabeth van der Woude,1657-1698 年)的日记,其中不乏某种风格)之外,最重要的是奴隶制问题激发了某些作家的创作热情。我们还可以提到英国女作家阿芙拉-贝恩(Aphra Behn,1640-1689 年),她于 1688 年出版了《Oroonoko 》一书,描写了非洲人伊莫因达的悲惨命运,他是三角贸易的受害者,因为他被情敌出卖了;当然还有伏尔泰(Voltaire,1694-1778 年),他的名著《坎迪德》(Candide,1759 年)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苏里南奴隶。让-加布里埃尔-斯特德曼(Jean-Gabriel Stedman)是 1744 年出生的一名军官,父亲是苏格兰人,母亲是荷兰人。他曾于 1772 年至 1777 年间参与镇压苏里南的奴隶起义,他在书中描述了所遭受的虐待,该书被多次翻译和重印,并配有明确的版画以强化其信息。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获得他的法文版《苏里南之旅》,但我们还是可以在《L'Harmattan》出版的克里斯托弗-格罗西迪埃(Christophe Grosidier)的历史小说《Capitaine Stedman ou le négrier sentimental》中了解他的生平。在《Het Surinaamsche Leeven》一剧中,作者(至今仍不为人所知)描绘了一个唯利是图、毫不妥协的讽刺社会。与此同时,另一部匿名小说《一个黑人的故事》(Geschiedenis van een neger)也问世了,在这部小说中,一个白人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特别聪明的黑人,这也许是受到了备受指责的格拉曼-夸西(Graman Quassi,1692-1787 年)的启发,夸西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,后来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,并代表殖民政府猎捕逃跑的奴隶(马伦人)。同样,1764 年《De Denker》杂志刊登了一些非常神秘的信件。这些信的署名也是卡克拉-阿科蒂(Kakera Akotie),他说自己曾在苏里南被卖为奴隶。他的身份一直受到质疑,但如果属实,他将是苏里南第一位非洲裔作家。
表明身份
诗人伊丽莎白-玛丽亚-波斯特(Elisabeth Maria Post,1755-1812 年)的《莱茵哈特》证实了这一点,与此同时,岛上的知识分子生活也在日益发展。大卫-纳西(David Nassy,1747-1806 年)于 1789 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《苏里南殖民地史论》(Essai historique sur la colonie de Surinam)。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,尤其是在戏剧方面。此外,在保罗-弗朗索瓦-罗斯(Paul François Roos)、雅各布-沃根-范-恩格伦(Jacob Voegen van Engelen)和亨德里克-舒腾(Hendrik Schouten)等人的倡议下,新的报刊杂志出现了,图书馆于 1783 年落成,文学界也纷纷成立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三个人都出生在荷兰,但却在苏里南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这表明了他们对新国家的眷恋,同时也表明,从文化的角度来看,尽管荷兰语仍然是苏里南的主流语言,但这块殖民地已经开始解放自己。1878 年颁布的《公共义务教育法》是一个新的里程碑,因为在此之前,除了富裕殖民者的子女外,海外领地还没有任何教育使命。同样,克里斯蒂娜-梵高开始为年轻人写故事。
然而,随着 1863 年奴隶制的废除,十九世纪和文学迎来了一个转折点,正如两年前出国的 Cornélius van Schaik 牧师所预见的那样。他的小说《De Manja》不仅描述了种植园的衰落,还包含了大量的斯拉纳语对话,夸米纳(A. Lionarons 的笔名,1827-1913 年)也使用了这一技巧,他可以说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本土作家:他在苏里南出生并去世。在《杰塔》(Jetta,1869 年)和《南尼》(Nanni,1881 年)中,他描述了他所处的时代,当时的经济正在寻求自我革新,同时唤起了一个富有的黑白混血女人的爱情故事。不可否认的是:写作与人物相互交融,社会与作家也是如此。例如,马塔瓦伊传教士约翰内斯-金(Johannes King)沉溺于自传,在数千页完全用斯拉南语写成的作品中,讲述了他和他的人民的生活,描述了他的梦想和幻觉。
在向二十世纪过渡的过程中,仍然存在着令人讨厌的怀旧情绪--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苏里南,有些人对奴隶制感到遗憾,并继续发表种族主义言论--但现代性正在前进。随着现代性的到来,某种现实主义有时也会变得尖锐,比如在小说《Een Beschavingswerk》中,理查德-奥弗拉尔(Richard O'Ferral,笔名Ultimus)嘲笑政府的自大狂;在诗集《Matrozenrozen》中,乔治-鲁斯特韦克(George Rustwijk)感叹荷属圭亚那与法属圭亚那和英属圭亚那相比的现状。至于路德维格-欧内斯特-蒂姆(Ludwig Ernest Thijm),他创作了一些流行歌曲,其中一些歌曲使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,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之间缺失的联系。诗人欧仁-雷勒姆(Eugène Rellum,1896-1989 年)则没有做出选择:他用荷兰语和斯拉南语写作。最后,获得自由的奴隶之子安东-德-科姆(1898-1945 年)在大洋两岸都生活过。他是非殖民化的狂热倡导者,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运动的成员,他的著作《我们,苏里南的奴隶》(W ij slaven van Suriname)于 1934 年出版了删节版,至今仍是一部经典之作。几年前,阿尔伯特-赫尔曼(1903-1996 年)出版了一部谴责殖民者剥削苏里南的小说《西苏里南》(Zuid-zuid-west)。约翰娜-舒腾-埃尔森豪特(Johanna Schouten-Elsenhout)以及后来的亨利-弗兰斯-德-齐尔(Henri Frans de Ziel)也致力于独立的新思想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美国士兵的接触加强了这一思想。
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
1954 年,荷兰给予苏里南自治权。在这十年间,苏里南的文学生活在经历了战时的阴霾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:流亡作家纷纷归来(如阿尔伯特-赫尔曼(Albert Helman),他后来成为了部长),读者群不断扩大并呈现多样化,《Foetoe-boi》杂志完全致力于克里奥尔文化,新的语言也开始崭露头角,如印地语,这要归功于未来的Gaanman Gazon Matodja奖得主巴伊(Bhai,1935-2018)。在政治层面,是诗人们宣布独立的愿望不会枯竭,如米哈埃尔-斯洛里(Michaël Slory,1935-2018 年),尤其是 R. 多布鲁(R. Dobru,1935-1983 年),他与万-邦(Wan bon)一起重申了他对统一和自由的苏里南人民的梦想。
1975 年,苏里南终于获得了独立,随之而来的是一段严重动荡的时期,在此期间,作家们被迫保持沉默,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,文学生活又恢复了势头。正是在这一时期,辛西娅-麦克劳德(Cynthia McLeod)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历史小说《Hoe duur was de Suiker? 阿斯特丽德-罗默(Astrid Roemer)和埃德加-开罗(Edgar Cairo)--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声名鹊起--开始重新出版作品,前者出版了小说和自传,后者出版了诗歌和广播剧。许多女性的作品也开始崭露头角,在此不一一列举,我们可以提到埃伦-路易斯-昂布雷(Ellen Louise Ombre,作品有《Maalstroom》、《Negerjood in moderland》等)、安妮特-德-弗里斯(Annette de Vries)、伊斯梅娜-克里什纳达斯(Ismene Krishnadath,作为作家和编辑,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)和玛丽琳-西蒙斯(Marylin Simons,1959 年出生)。与她同时代的玛拉-基顺达贾尔(Mala Kishundajal)从事戏剧和小说等多种体裁的创作,并以移民为题材。最后,玛丽克-凡-米尔(Marijke van Mil)从十几岁起就生活在荷兰,她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,并从祖母讲给她的故事中汲取素材,创作了多部作品;卡琳-阿马特莫克瑞姆(Karin Amatmoekrim)也是一位外籍人士,她也从家族历史中汲取素材,创作了《Waneer wij samen zjin》一书,并在 2009 年凭借《Titus》一书获得了黑魔女奖。拉乌尔-德容(Raoul de Jong)的职业生涯证明,新一代艺术家正自由穿梭于两大洲之间。拉乌尔-德容 1984 年出生于鹿特丹,但他的父亲是苏里南人,他从未见过父亲,当他意外收到父亲的一封电子邮件时,他决定漂洋过海寻根。这次旅行激发了他创作《美洲豹》的灵感,该书由 Buchet Chastel 翻译成法文。